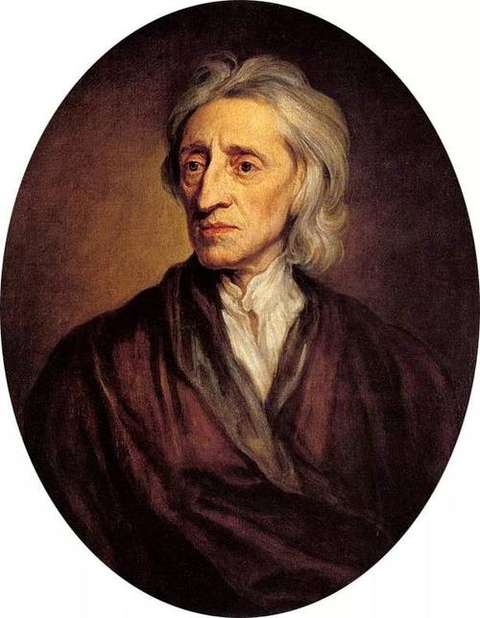
◎朱彦凝
巴西仓库剧团的《布拉斯·库巴斯死后的回忆》作为2023年乌镇戏剧节一票难求的热门剧目,近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。该剧以戏谑的方式展开沉重的生死议题,试图将百余年前的作品与当下社会达成对话,探讨现代人共通的生命体验,为中国观众带来了一场以往不多见的南美戏剧体验。
关于人生价值的哲思
《布拉斯·库巴斯死后的回忆》的作者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(1839—1908)被誉为“巴西文学之父”,这部小说是他从浪漫主义风格向现实主义风格转型的重要作品。巴西仓库剧团的文本改编并没有完全因循小说的叙事框架,呈现出两个主要的亮眼之处——三线并行的叙述方式和场景拼贴式的结构。它以“亡者库巴斯”的回溯讲述为主线,在“生者库巴斯”经历的人生片段之间,插入“小说家马查多”的反思、评论。
当亡者库巴斯开始用调侃的语言讲述自己“无意义”的一生时,已为作品奠定了荒诞的基调。从成长到死亡、从爱情到事业,库巴斯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显得乏味。剧中,布拉斯·库巴斯及其社交圈里的上流人士,完全无视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,沉浸在金钱、物质带来的快感中,认定有形的财富才是唯一具有价值的存在;同时没有长期的生活目标,随波逐流,浑噩度日,内心空虚焦虑。
有观众将此剧的剧情概括为“一事无成的男人和两个女人乏善可陈的故事”。这样的评价不无道理: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戏剧性强、情节紧凑集中、外在冲突明显的作品,这部剧更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,阐释关于虚无、生死和存在的哲学思考。
细心的观众能从葡萄牙语台词中听到一个单词反复出现:nada(意为无、没有)。这让人想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《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》,都表达着一种主观上的“什么都没有”。这种“虚无”的生存状态,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席卷欧美社会。欧几里得、牛顿、为代表的科学权威与黑格尔的“绝对理念”被重新认知,与小说作者马查多同时代的哲人尼采,恰在1882年(《布拉斯·库巴斯死后的回忆》小说写作期间)宣告“上帝已死”。此时,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崩塌,人们普遍陷入焦虑、荒诞,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何在。
巴西曾长期处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,马查多创作的年代正是巴西帝国走向巴西共和国的过渡时期,废奴运动、政治变革接踵而至,社会价值观变得分裂扭曲,这成为马查多在创作中叩问人生意义的时代背景。

“布拉斯·库巴斯膏药”
但是,无论是原著作者马查多,还是该剧的“戏剧构作”门多萨,都没有将目光局限在悲观的“虚无”之中,而是从中生发并探讨现代社会人们共通的生命体验。库巴斯与大多数人一样,面对生活的态度兼具积极和消极两面。有时他会从自我出发,主动介入生活,企图改变命运,如奋力争取与维吉尼亚的爱情;有时他的自我意识没有发挥作用,莫名其妙地被外力抛入洪流,如被父亲勒令立刻出发赴欧洲留学。

马查多的爷爷是被解放的黑人奴隶,但他不愿向人坦承自己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,因为这意味着更边缘的社会地位。身为工人的父母在他12岁那年相继去世,他成了一个孤儿。马查多感受到种族和命运让自己身处的无依之境——“没有我来自何处之根,也没有我去向何处之轨”。这就是存在主义认为的“此在在世”(人生活在与世界的联系中)的基本感受——孤独。当个人被规律抛弃、失去价值参照与身份认同时,他必然会感到孤独。这促使他创作出了鲜活的布拉斯·库巴斯形象——一个享乐至上、缺乏道德约束、外表光鲜实则内心孤独的贵族公子。
随之而来的是身份固化带来的不适、选择决定带来的焦虑和对“能够存在”的畏惧。当库巴斯难以忍受它们带来的痛苦时,他渐趋走向海德格尔所说的“沉沦”。他放弃了自己的主见,放弃了对常人社会的抵抗,按照父亲或他人提供的“做什么”和“怎样做”的标准行事。即使他内心深处想等情人玛塞拉一同去欧洲,但当父亲让他即刻出国读书时,他还是照做了;归国后,父亲告诉他,“结婚和从政绑在一个套餐里”,他也只得妥协。他认为自己此生最大的成就是发明了能有效缓解忧郁的“布拉斯·库巴斯膏药”,看似荒诞的背后是对自我的放逐:“沉沦”的库巴斯放弃了选择,也就没有了责任,避免了孤独,但长此以往势必会对一成不变的生活产生厌倦,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“真正的无聊”,从而启示人们正视自身存在的意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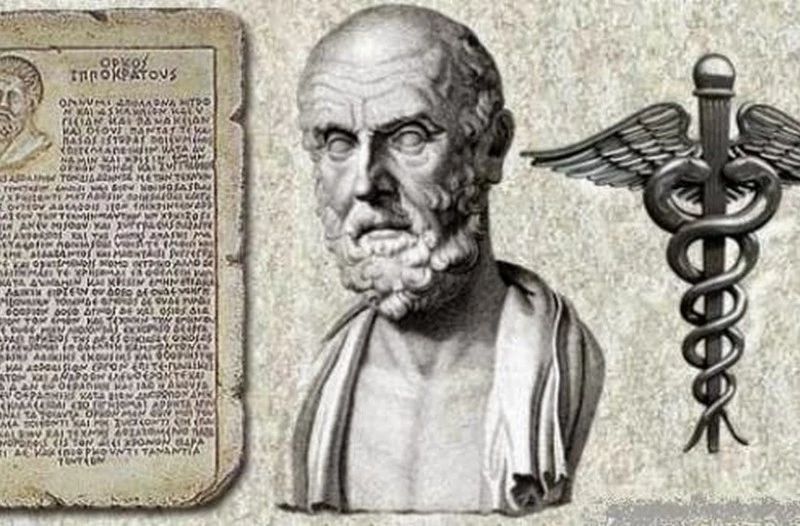

“渴望回到那一天”
从剧名不难看出,生与死的探讨是《布拉斯·库巴斯死后的回忆》的重要议题。海德格尔认为,在唤醒沉沦上,比无聊更有力的恰恰是对死亡的领会。自然女神在全剧首尾处分别对库巴斯说了一句话——“若你意识回归,你会发现自己渴望活着”和“你已经死了,你会渴望回到那一天”,前后呼应,带领观众思考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。随着一次次地见证死亡,库巴斯的态度也有所转变,由最初质疑“活着的意义”到最后发出了“活着真美好”的感叹。
年轻的库巴斯踏上前往欧洲的轮船时,因为被迫远离家乡、与爱人分别,一时冲动想跳海自杀,但被船长拦了下来。此时的他依然处于沉沦的状态里,既没有找寻到生活的价值,也没有认识到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很快,暴风雨来袭,整条船上的人命悬一线。当死亡真正逼近,库巴斯深陷绝望与畏惧。船长夫人的去世让他清晰地认识到,没有人能永恒存在,死亡意味着烟消云散。此时的他与常人一样,都是畏死的,想要极力避讳死亡。但死是逃不脱的。真正唤醒库巴斯的是他母亲的骤然离世——他第一次目睹至亲死亡。这使他震颤,将他从沉沦中唤醒,他由此认识到了生的弥足珍贵,走向澄明。

所谓澄明,就是人提起存在的勇气,正视自己,应该本真地活着,应该具有孤独感。海德格尔写道:“他在时间中生存。他承认自己站在一条曲线的某一点上,承认他必须走到终点。他隶属于时间,而且由于附着在身上的恐惧感作祟,他认准了最邪恶的敌人。明天,他向往着明天,但自身的一切却拒斥着它。肉体的反动正是荒谬。”(《存在与时间》,海德格尔)
在《布拉斯·库巴斯死后的回忆》中饰演小说家马查多的演员,在黑板上写下了醒目的“在我死去之前,我想……”,这恰恰是接受了死亡的必然性,并且珍惜自己的存在、充分发挥主体意识的表现。布拉斯·库巴斯这一生或许是“一事无成”“乏善可陈”的,对爱情和事业都求而不得,但他仍在将死之际发出“活着真美好”的感慨,与此同时,舞台上的其他角色——还在沉沦中的人,却埋怨“活着真没劲”,对现代人命运的关怀、对全人类未来的忧虑,都蕴含其中。摄影/王大威





